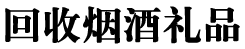行走于东西方之间——康熙时代的西方友人们
1661年,15岁的莱布尼茨在莱比锡大学读书,25岁的路易十四开始亲政,8岁的康熙则刚刚登基。
1666年,莱布尼茨拿到博士学位,并出版了第一部哲学著作《论组合术》。路易十四则在本年创建了罗马法兰西学院,踌躇满志于“文化国家化”的宏愿,并使之制度化,以国家资助的方式,将文化名流以及各种人才纳入国王彀中,为他的国家服务,这一切的动力,恐怕来自对中国皇帝治下的向往。而少年康熙的同时期,正在上演着宫斗剧,捉拿权臣鳌拜,开始亲政。
莱布尼茨生活的时代,是君主制世界最好的时代,他与康熙和路易十四并世而立,从路易十四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康熙帝对西方科学的追求中,他一定看到了东西方文明之“前定和谐”的前缘,在世界文明的两极对话中,他放眼展望大同世界。他以哲学家的眼光,目睹了欧洲1718世纪从东方舶来的文化调性,看到了好君主开明君主制,带给人类的希望,他并没有生出多少对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或欧洲更多的期待,反而是在仰慕东方的康熙皇帝时,唯恐欧洲滞后于历史。
就像跨栏赛跑,他们在跨越世纪之初后,便各安天命了,莱布尼茨逝于1716年,路易十四逝于1715年,康熙逝于1722年。当我们用莱布尼茨的视角把东西方的时空串联起来时,发现历史逻辑的奥妙即文明转型,必假以几个天才般的历史人物的引流,还要假以时日的历史演练,因为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那时的欧洲,正处于民主前夜的君主时代,寻找一种更好的君主制度,还是哲学家们的执念,如莱布尼茨就表现出了对东方君主制的极大热情。他说,天意要让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地域相隔最远的民族携起手来,使得位于它们之间的各个民族都过上一种更为合乎理性的生活,他称“支那”为“东方的欧洲”。
同路易十四对中国皇帝的憧憬相比,康熙帝则更多关注西洋人的实用科学和实用艺术,他们皆为对方所吸引。
1687年,路易十四以“国王数学家”的名义,派遣五位耶稣会士前往中国,并给康熙帝送去30箱科学仪器。
洪若翰、张诚、刘应、白晋、李明五人,因科技精湛,在紫禁城被康熙帝召见,尤以白晋对康熙帝影响最深。随后,张诚、白晋分别为康熙讲授测量学、几何学、解剖学等科学知识。
1693年,康熙帝罹患疟疾,法国人进献西方特效药金鸡纳霜,引起他对西医药的重视。1697年,康熙派白晋返回法国,希望他募集科学著作以及征求来华科学家。期间,白晋写作《中国皇帝康熙传》,路易十四正是通过这本书对康熙有了初步了解。《耶稣会士中国通信集》,被欧洲人看作是启蒙时代最好的百科全书作品之一。由巴黎耶稣会总会长兼中国耶稣会总办郭弼恩编辑,从1702年到1776年,共编辑了34卷,收集了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白晋、马若瑟、宋君荣、冯秉正、沙守信、傅圣泽等法国耶稣会士的通信。郭弼恩在编辑并出版了八卷后去世。杜赫德后继,再编辑并完成了从第九卷到二十六卷的出版,后续,又有他人出版若干卷。看得出,《通信集》是欧洲人在比较东西文明异同的过程中,第一次尝试更为理性地反省自身文化存在的问题,同时,他们在康熙帝和路易十四之间,搭建了一座通畅的文化桥梁。
当然,两大文明的“互动互译”早在法国之前就慢慢的开始了,德国人汤若望,1620年就来到了澳门,那时他27岁,从此,直至去世,他都没有离开中国,在异国他乡整整生活了47年,可完全说中国是他为之投注所有生命热情的第二故乡。
汤若望以一身的博学,侍奉了明、清两朝,除了传播基督教的福音文化,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参酌西洋历法修订中国历法,还有就是铸造大炮,这两项成果,皆完成于崇祯年间。
1634年,他协助徐光启完成《崇祯历书》,共计46种,137卷,它标志着中国的天文历法开始了跟世界的接轨。清初,他又重新修订“崇祯历”,进呈摄政王多尔衮,更名为《时宪历》,封面刻有“依西洋新法”字样,颁行天下,成为各地农时的天文依据,由此,清廷命他为政府钦天监监正。
可《时宪历》一问世,就遭遇了朝臣杨光先的攻击,他留下一句:“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此话听起来荒唐可笑,却至今耳熟,其余音,每每凛然唾液星溅,致晚清史劣迹斑斑,成为历史上一个口号式智障标记。
更有甚者,杨光先不但撰文《辟邪论》,还诬告汤若望谋反,必欲除之而后快。鳌拜执政期间,杨光先达到了目的,汤若望被判凌迟罪,幸得孝庄皇太后斡旋得以留存性命,但追随的同僚必须为这场历法之争付出生命的代价,史称“康熙历狱”。
不过,最搞笑的是,清廷一再提拔杨光先为钦天监监正,但他自知不懂历法,也一再坚辞不就。清廷不允,无奈,他只好再推举一个副监负责历法推算,以旧历取代《时宪历》。
不久,鳌拜倒台,康熙帝亲政,清廷重启《时宪历》,少年天子,青春无敌,尤重西学,为汤若望。五年后,这位继利玛窦之后来华传播西学的文明使者,安然逝于南堂。
比利时人南怀仁于1658年来到中国,1660年,他前往北京,参与汤若望修订历法,因受牵连而入狱。1668年,应帝诏被重启,开始节录艾儒略《西方答问》,编著并更名为《御览西方要纪》,进呈清廷。1669年,受帝命,掌管钦天监,原钦天监监正杨光先被革除。1678年,南怀仁开始做蒸汽动力试验,并着手翻译科学文献,在葡使傅汎际与明朝大臣李之藻合译的逻辑学著作《名理探》20卷的基础上,续译改编为60卷的《穷理学》,于1683年完成,并进呈给康熙。
1662年,葡使郭纳爵、意使殷铎泽,合译了儒家“四书”中《大学》部分,还将《论语》译成拉丁文,取名为《中国智慧》,成为第一部中文与拉丁文双语对照的儒经译著,也是首个从左至右横向排版印刷、以及最早使用圆弧括号的出版物。
1687年,法使柏应理与人合译“四书”,在巴黎印行,译名为《中国哲学家孔子》,附《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文译本。1711年,比利时人卫方济在布拉格大学刊印《四书》译本,系统介绍儒家经典,为欧洲最早《四书》全译本。
1712年,法人恩脱雷科利斯(Entreecolles)撰成《中国陶瓷见闻录》,由法国耶稣会出版,引起欧洲社会兴趣。
更为有趣的是,翻译《四书》与介绍中国陶瓷书籍以及中医药书籍,对于欧洲,可谓接踵而至,他们用来解决欧洲人的国计民生问题。何以言之?当时欧洲最大的国计,莫过于解决开明君主制的问题,而《四书》则为此提供了一个中国解决方案。
民生之大,对于当时的法国来说,莫过于餐具之于食品安全问题。当时欧洲瘟疫频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没有安全的餐具。其时,法国国库亏空,国王路易十四为了削减开支,主动将银质餐具换成相对廉价的陶瓷餐具,还专门向鲁昂陶瓷厂订购彩陶餐具,倡导臣民举国效仿,引领餐桌革命风尚。
在欧洲,法国首先开始普及并推广以陶瓷取代金属餐具的餐桌风尚,不仅给欧洲带来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人类卫生以及餐饮文明的进化,都具有划时代的史诗级别的启蒙影响。
银质餐具昂贵难以普及于社会,而广泛使用的木质餐具又容易滋生细菌,锡金属餐具含有重金属超标的潜在威胁,玻璃餐具则尤其易碎、遇高温易裂、烫手等,这样一些问题始终是欧洲餐饮进化中的“疑难杂症”。欧洲中世纪的几次大的流行病,与餐饮器具的使用习惯不无关系,以至于令今人谈瘟疫而色犹变。
试想,如果中国人没有发明陶瓷,路易十四的人生光谱上没有陶瓷,欧洲人的餐桌上没有陶瓷,那么关系到人的生存根本的、餐桌上的人类文明进化史将如何书写?路易十四的花式抱负又该如何抒写?欧洲人的护生饮食将会终结在哪一种餐具上呢?没有办法,历史发生了,我们的提问只能如解玉砂般愈发把历史琢磨得剔透如青花瓷,时间不可逆,直到今天,瓷器仍然是餐桌上最好的餐具。
而中国方面,对于欧洲的需求,在民间立场,除了白银,还是白银,以至于在全球史上,造就了一个“白银时代”。
之于中国朝廷,则不止于白银,还多了一点科技,帝谕:西洋人有技艺巧思者或内外科大夫,急速差人送京。
1719年,中国首份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成书,历时30余年,在法国人的参与下,辗转各地完成实测,这是中国第一部通过实测、采用经纬图法、梯形投影绘成的全国地图集。1737年,《中国新图集》于巴黎出版,图集纵52厘米,横38厘米,收黑白图42幅,此图正是依据康熙年间的中国实测资料编制而成。
这样,一批行走于东西方之间的文明使者,不但在促进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方面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还在国际关系方面,协调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并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1689年,康熙帝派出他非常信任的法国人张诚,协助索额图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边界归属。
在《中国近事》的序言中,莱布尼茨特别提到两位法使徐日升和张诚,应康熙之邀,由太阳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在中俄两国之间斡旋沟通,为条约签订发挥了重要作用。
《尼布楚条约》将世界两大文明中心中国与欧洲,通过一条正在进行时的文明开化带俄国,不仅以地理政治学的方式,更以文明会通的方式,连接起来。当时,欧亚三个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帝国,都投入到条约中来了,康熙帝和彼得大帝作为两个当事国代表,路易十四则以派遣传教士的方式参与。
这是中国与近代主权国家间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在条约中,“中国”第一次作为主权国家的国号,出现在一个国际化的条约里,不是作为中国传统里的那个天朝体系,而是被“欧洲共识”所认可。被《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所接纳的“中国”,是用满、蒙、汉三语统称的“中国”,在划分疆界与人民归属时,“条约”中使用了“中国”与“中国人”,中方首席代表索额图的全衔是:“中国大圣皇帝钦差分界大臣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国际条约中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中国”在条约里,用拉丁文译作“Dulimbaigurun”(直译是中央之国),立界碑时,条约规定要用拉丁文、俄文和“中文”镌刻,“中文”非独汉语,还包括了满语和蒙语,故界碑一面是拉丁文和俄文,另一面为满、汉、蒙三种文字。
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后因世界历史中心的转移以及中国的历史地位被一而再边缘化而忽略。
当欧洲人通过传教士发现一个与他们迥异其趣却可以并论的中国时,与之呼应的作为丝、瓷、茶的母国的反应是开放的。似乎这时不同文明之间,尚未分泌谁优谁劣的文化情绪,心理落差也并不明显,对待异域文化饶有兴趣并关注学习。
雍正以后,欧洲由君主制国家转型为近代化的君主立宪制或民主制的民族国家,而王朝中国却未发生这样的转型,传统天下观无法应对新世界格局,于是,开始排斥和封闭,形成一个作茧自缚的内卷闭环。
还有另外一种“隔代呼应”,风起云涌于一百年以后。18世纪启蒙时代,欧洲面临“中国乎?希腊乎?”19世纪中叶,战争以后的中国其实也面临同一问题的选择。
选择希腊,意味着民主制,选择中国,几乎能肯定,那个被欧洲看作君主制理想国的康熙时代,已然过时。即便是康熙时代,那也不过是开明君主专制,在那个君主制的盛世,连历史都还没有准备好给中国出选择题,不着急,历史会给出选择的,19世纪末,是全世界君主制的末日。
若想看君主制的盛世风景,不妨从黑格尔和谢林对中国“冷”批判上溯至莱布尼茨的“热趸”,就会发现,这位哲学前辈的中国灵感,与路易十四的“中国热”的一致性,甚至超过传教士,并为欧洲的“中国热”提供了一个形而上学的憧憬。
就像大航海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康熙盛世,是欧洲人发现的一座“文化新大陆”,康熙帝为欧洲提供了一种君主立国的理想样式,他开放包容,不断学习,其麾下,儒士、教士统用,中学、西学齐上。“太阳王”路易十四与康熙大帝,法国与清朝,在东西方各自的天际,露出一抹新王朝的帝国使命感。
路易十四,完成了黎塞留和马扎然的遗政,实现了绝对中央集权,历经战争考验,赢得欧陆霸主地位。战争、扩张以及因强大催生的荣誉,额外刺激了路易十四的艺术激情,太阳王的浪漫,风靡了一个时代,连充满血腥的战争都被他风格化了。正如他在芭蕾舞中扮演的太阳神阿波罗神那样,以艺术之神的名义,他创造了全世界对于文明与生活的无限想象,他对东方宫廷的倾心向往,其灵感来自于他要再造一个具有艺术品位的君主世界。
而对于康熙来说,似乎皇帝的一切也并非都是被允许的,他的自律,为君主蒙上了儒教圣王色彩,他懂得妥协,必须勤治,才能在大明皇帝的宝座上,坐稳爱新觉罗氏的天下。他还知道,天下不只有大清,大清之外,还有好多个“天下”,中国境内就有西洋布道之士行迹宇内,振铎之声响彻深山。当文明的使者来到大清国时,他未禁止他们传道受业,而是向他们开放。
欧洲同样流行“中国风”。欧洲的艺术家们也热衷于“中国风”的艺术创作,从当时获得巨大成功的挂毯艺术作品中,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路易十四对世界那一边的中国的向往。
名为“中国皇帝”的系列壁毯,是典型的臆想中国皇帝日常景象的最早一批作品,大约在17、18世纪交汇时,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举办了名为“中国皇帝”的舞会,由皇家博韦作坊(Manufa-cyureRoyaledesBeauvais)制作了这批艺术挂毯。
壁毯作品,共有九件,分别为:《皇帝出行》《皇帝上朝》《皇帝登舟》《皇后登舟》《皇后茶饮》《狩猎归来》《天文学家》《采菠萝》《便宴》。要做就做得最好,那些博韦皇家艺匠们,使这组挂毯与同一时期的特里阿农瓷宫成为整个巴洛克时代中国风艺术的精品,影响颇广。
法国哥布林和博韦的挂毯厂,分别于1662年和1664年建立,博韦从1688年开始生产“中国皇帝”系列挂毯,直到1731年停产。挂毯六联组合,十幅共十个场景,由三位艺术家设计:盖路易韦尔纳萨、丰特纳、芭蒂斯特莫努瓦耶。其中挂毯《天学传概》表现了教士汤若望和南怀仁在清廷的活动。
九件挂毯,除了帝、后反复出现之外,竟然别有一帧,让给了“天文学家”,显得特别耀眼,表明路易十四对康熙帝看得很准,他深知康熙帝所好在天文。
康熙帝看世界,看的是他能看懂的和他需要的。他对西方天文学的兴趣,恰恰表明了清王朝从“逐水草而居”的马上习俗向“安居乐业”的农耕文化的转型和认同,农耕文化最高级的哲学智慧,就是人文关怀要在参与自然造化的运行中显现。
尽管人类是从自然之中异化出来的力量,但毕竟还是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人类据守的底线。“天”,在中国文化中,作为自然的最高代表,居于人的精神之巅,帝为“天子”。“赞天地之化育”,是天之子的最高职责,顺因自然,也就成为了农耕政治文明的本色。因此,每一位皇帝,都会关心天文和历法,亦为皇家钦天监的职责。
除了观察天象、推算节气、制定历法的需要外,皇帝的政治命运与天象变幻有着贞卜的神秘意蕴。所以,康熙帝格外重视西学中的天文技术,天文学家也就成为东西交流的桥梁。
在法国,几乎所有的陶器工厂都在尝试研制中国瓷器的陶土以及工艺,蓝调上加五彩,花草植物藤蔓妖娆,抒情、诗意、浪漫等艺术气质,舒缓了来自荷兰怪异夸张的神秘趣味,丰富、奢华、端庄,构成了法国巴洛克时期中国风瓷器特征。
1664年,路易十四开始修建他父亲在巴黎近郊留下来的行宫,直到1689年竣工,整整用了25年的时间,建成一座举世无双的宫殿,这座具有浓郁东方情调的巴洛克风格的宫殿,就是凡尔赛宫,路易十四终于在其本土再现了对东方奢华的想象。
1670年,路易十四委任建筑师路易勒沃,在凡尔赛宫苑中建造了特里阿农瓷宫,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情人蒙特斯潘夫。据说设计灵感来自荷兰人纽霍夫《荷使初访中国记》一书中的插图《南京大报恩寺疏璃塔》。
当然,瓷宫与寺塔风格相去甚远,可能因为南京大报恩寺塔在当时的欧洲影响太大了,但凡与中国风“沾亲带故”的建筑,坊间都会不吝笔墨地往上靠,随风传遍欧洲。不过,捕风还是能捉到影的,瓷宫虽然是单层建筑,并非塔状,但瓷宫内外,为模仿青花瓷,使用了大量的蓝色和白色陶砖装饰,建筑外层的陶瓷带有彩色釉面,产自代尔夫特、韦尔、鲁昂和利雪。
特里阿农瓷宫,这座雄伟的建筑是欧洲第一个巴洛克中式风格的行宫。作为巴洛克“中国风”的表现,它初露端倪,便成经典,引领并定调欧洲时尚东方帝国的豪华样式。不过,终究是因为它的维护成本极高,到1687年,就被拆除了。但这依然影响不了路易十四“攀比”他臆想中的“中国皇帝”的高涨情绪,1700年1月7日,他在凡尔赛宫,举办了名为“中国皇帝”的盛大舞会,服装和舞台设计灵感,大多数来源于中国戏曲的启发。如此风光,想必让太阳王路易十四以为在他的凡尔赛宫里,就已经能毫无遗憾地可与“中国皇帝”比肩了。
在太阳王狂热于中国瓷器之际,康熙帝也被法国玻璃工艺吸引,在内务府建立了琉璃和珐琅彩工艺作坊。
19世纪,随着康熙时代早已过去,冷却了欧洲的“中国热”,流行一转,从“中国热”转向了批判“中国热”。“希腊乎?中国乎?”两个古老的文明,接受了欧洲“文明公投”的选择,东方君主制和王朝中国落选。
(作者近著《走进宋画10至13世纪的中国文艺复兴》,北京时代华文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