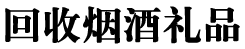纪念︱从境地研究到气候史:勒华拉杜里的总体史探索
法国的气候史研究由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史家勒华拉杜里所开创和引领,后吸引历史学、地理学、气象学及文学界的学者加入其中,相关研究成果与发展形态趋势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关注。关于法国气候史研究的缘起和发展,国内外学界尚不进行系统研究。有的学者把法国气候史的缘起放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环境史发展的脉络中进行论述;有的学者觉得勒华拉杜里在20世纪60—70年代所倡导的“没有人的气候史”,使法国环境史研究滞后了25年;也有的学者觉得,勒华拉杜里的这一倡议背离了年鉴学派的境地研究,终结了年鉴学派的总体史。上述学者的认识均存在偏差,一是没看到年鉴学派的境地研究与气候史的渊源关系,二是误解了勒华拉杜里提出的“没有人的气候史”的初衷和旨意。近年来,勒华拉杜里本人在著述和访谈中,多次谈起其气候史研究的缘起和历程,对他当年提出“没有人的气候史”的初衷和后来的改变做出了一些解释,但并没有谈及他的气候史研究与年鉴学派境地研究的关系,也没有详述欧洲他国的气候史研究对他的气候史研究转型的影响。笔者拟将勒华拉杜里的气候史研究放到年鉴学派的发展脉络中论述,并考察其受到的欧洲他国气候史研究的影响,从整体上把握勒华拉杜里气候史研究的转向,挖掘其背后隐藏的总体史追求。
法语中的“境地”(milieu)一词源于牛顿物理学的“媒介”(medium),也就是“以太”(éther),即流动的介质,能使一个物体对不相连的另一个物体施加影响。直到18世纪,“境地”一词都带有物理学含义。狄德罗和达朗贝尔主编的《百科全书》设有词条“境地”,将其定义为“身体所处的物质空间,并有可能是在其中进行移动”。19世纪初,拉马克(Lamarck)将该词引入生物学领域,多使用境地的复数形式“milieux”。1848年,孔德的学生夏尔·罗班(Charles Robin)发明了“环境学”(mésologie)概念,主张把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万物看做一个整体。随后,孔德把“环境学”定义为“对境地的理论研究”,认为“境地是有机体的主要调节器”。19世纪末,维达尔·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赋予“境地”以地理学含义,指出人是地理境地(milieu géographique)的组成部分。白兰士对人与境地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思考。他反对德国人文地理学创始人李特尔(Allemands Carl Ritter)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所提出的社会现实依赖于境地的观点,主张人是境地的重要的因素。他认为,在自然的作用和人文现实之间,人类能自由地主宰。自然往往提供多种可能性,供人类选择。这种论点被称作“或然论”(possibilisme)。
年鉴学派的创始人费弗尔和布洛赫都对境地做过重要研究。费弗尔著有《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他顺着白兰士的思路攻击当时仍占主导地位的地理决定论,建议把地理学定义为对居所研究的科学(science des lieux)。他认为,地理环境只是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条件,而不是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原因。但他还认为人与境地的关系极为密切:“在作用于境地的时候,人类不可能置身于境地之外。人类在试图对境地施加作用的同时也必然受到境地的反作用。而影响并制约了人类社会生存的自然界,也不是外在于人类作用的处女地,它已经被人类深刻地影响、变更和改造过了。”布洛赫在1931年出版的《法国乡村历史的特征》中,用长时段和回溯方法研究了土地占有、人口密度、居住方式、小块土地与农业技术的关系、景观变迁等,探讨了人和境地之间多种多样的关系。他认为,大自然加之于人类活动的条件有助于解释法国不一样的地区的差异。例如,洛林的大村庄周围是无圈围的长条田,布列塔尼到处都是圈地和农舍,普罗旺斯的村庄像古希腊卫城,朗格多克和贝里有很多不规则地块。
布罗代尔吸收了法国地理学对人与境地关系的研究,提出了地理历史学(géohistoire)的概念。他指出:“社会生活由自然和生态因素决定;它与后者产生联系,进行合作,后者改变、助推或影响一个社会的生活,因此它的历史……我们提议称之为‘地理历史学’。”他指出,地理历史学反映出两种可能:一方面,自然变化能改变人类历史进程;另一方面,人类根据境地提供的可能性建构历史。此外,布罗代尔受到德国地理学的影响,阐明了经济和社会的关系在空间的展现,考察了资本主义企业促成的国际网络在地中海这一空间的确立,探讨了民族国家取代城市国家的过程。
布罗代尔在博士论文《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以下简称《地中海》)中,描述了地中海的山脉、高原、平原、海域和沿海地带,探讨了在地中海的自然单位内气候与历史的关系,阐释了地中海的区域内道路与城市、人员流动、货物运输、疾病流行以及贸易经济发展形势。布罗代尔此书提供了境地研究的范本,即把境地当作一个几乎静止不变的空间,看成人类活动的场地;人类和境地紧密联结,相互作用。此后年鉴学派的著作,尤其是拉布鲁斯20世纪50—60年代指导的那批社会经济史的博士论文,大都以境地研究作为第一部分。例如,古贝尔1960年出版的博士论文《1600—1730年的博韦和博韦人》,第一部分以“结构”为标题,探讨了15世纪博韦社会的主要特征,描写了博韦的地理风貌以及同时代人对博韦的看法,阐述了博韦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乡村和城市社会。第二部分才是“局势”,讲述了1600—1730年博韦的经济、社会和人口波动。
为了更好地揭示境地研究的特征,我们大家可以借助梅雪芹教授对境地研究与环境史差异的分析进行说明。第一,在布罗代尔笔下,境地置身于时间之外,是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地理环境不过是人类活动的场所或舞台。而在环境史学者笔下,“自然”不只是供人类活动的前提、工具或舞台,它还是影响历史进程的一个活跃因素,是人类社会变迁的能动因素。造成这一区别的原因主要在于,年鉴学派的思想渊源或理论基础之一是地理学,而环境史研究的思想渊源或理论基础之一是生态学。第二,环境史是研究由人的实践活动联结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互动过程的历史学新领域。环境史中作为互动一方的“自然环境”不包括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但是互动另一方的人类社会囊括了人工环境和自然环境。而在境地研究中,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密不可分,不论是人文地理学者还是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都没有把它们分开探讨。因此,要让气候成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就需要将气候从境地研究中分离出来,把它当成不断对人类社会施加影响的外在的独立因素。
气候是地理学探讨的内容,也是境地的一个要素。但自古以来,文人学者都认为气候稳定不变。在古代西方,气候是地理概念。古希腊人认为,由于太阳对地球光照倾斜角度不同,气候一般随纬度和季节变化;气候即指两条纬线间的带状区域。从希波克拉底到亚里士多德,一直到1694年《法兰西学院词典》依旧把气候定义为“两条纬度之间的地带”。法兰西科学院也认为,气候指的就是赤道上两个平行圈之间的地带。到了18世纪,随着现代气象学的孕育,气候的定义发生了变化。1762年《法兰西学院词典》在气候的地理含义中加上了天气状况的概念。自此,湿度、温度和大气成分成为气候的基本要素。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着重探讨调节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尤其是造成不一样地区气候差异的机制。菲斯特于1845年发表著作《法国气候的变化:气象革命史》(Des Changements dans le climat de la France:Histoire de ses révolutions météorologiques),借助葡萄采摘日期、葡萄酒的品质、冰川的演进以及极端气候事件的史料,论证出历史上有两个气候变动时期:从恺撒时代到6世纪,气候逐渐变暖;从6世纪到10世纪,尤其是查理曼去世后,气候普遍变冷。随后,气象学家安戈(Alfred Angot)用第戎(Dijon)、萨兰(Salins)、欧邦讷(Aubonne)的葡萄采摘日期系列,探讨历史上的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但这些新见不但没有促成学界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共识,有时还会引发轩然。直到20世纪中期,法国学界基本上还是认为历史时期的气候一成不变。气象学家指出,“一个地方只要有三十年的记录,便可以认为这三十年的平均气温和雨量代表这一个地方历史时期的气温和雨量的标准状况了”。在关于境地研究的著作中,不管是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问题》,还是费弗尔的《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都把气候当作境地中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要素。
值得注意的是,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中,对气候的认识已有两点突破:第一,布罗代尔指出,“天空独立于当地的自然条件。地中海的气候受外界两股大气流的影响:来自西边邻居大西洋的气流和来自南部邻居撒哈拉沙漠的气流。地中海的万里晴空不由自己所决定”。这表明他已经把气候当作对境地施加影响的外在力量。第二,布罗代尔预测气候在历史时期有变化。该书第1卷第4章《作为一个自然单位的地中海:气候与历史》中,有一个小标题即“16世纪以来气候改变了吗?”布罗代尔指出,没有人再相信自然地理一成不变。阿尔卑斯山山脉有移动,地中海海岸线有变迁,气候现象可能也是如此,而且已得到大量文字资料的证实。但气候波动的周期和方向问题仍留待解决。
勒华拉杜里在巴黎高师读书时,选修了让·默武莱(Jean Meuvret)的课程,听他多次讲到16世纪末期和17世纪的经济危机。1955年后,勒华拉杜里跟随拉布鲁斯做博士论文,选题是“朗格多克的乡村社会”。他在16—17世纪法国乡村的土地册等档案中发现了丰富的气候信息,意识到气候对农业社会的重要性。这些都启发他发展布罗代尔的思路,论证气候的变化与17世纪经济危机的关系。
怎么论证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呢?1955年,勒华拉杜里读到阿尔贝·迪克罗克(Albert Ducrocq)论述树木年轮的文章和马塞尔·加尼耶(Marcel Garnier)论述物候学对研究气候波动的贡献的文章,也读了一些讲述17世纪冰川微弱增长与20世纪冰川消退的文章,认识到年轮学、物候学、冰川学是研究历史时期气候波动的有利途径。
此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社会经济史学界形成的生态—人口模式也有助于勒华拉杜里突破境地研究的框架。20世纪上半期,经济史学家弗朗索瓦·西米昂(François Simiand)认为,1630年左右,欧洲的商品从价格持续上涨进入价格停滞时期,还在于贵金属输入减少了。而在这期间工薪阶层成功地应对了这一打击,其经济活动也呈现出创造性。20世纪50年代,肖努夫妇(Pierre and Huguette Chaunu)对西班牙与美洲商业交往的研究推进了西米昂的观点。但古贝尔在《1600—1730年的博韦和博韦人》中改变了这一论证的方向,他否认西米昂所说的经济创新,而是认为17世纪中期欧洲的商品的价值普遍下降是经济困难的标志。这一时期生产下降,收入减少,经济停滞,他称之为“悲惨的17世纪”。古贝尔对这一状况的解释,转向了完全不同的气候和人口方面。他认为,17世纪欧洲的经济情况反映了“一种不规则的食物供给和人口增多之间的阶段性不平衡”,而天气是影响农业产量的主要的因素;有可能存在一个30年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周期。
勒华拉杜里继续推动古贝尔的史学转向。他在《朗格多克的农民》第一部分“马尔萨斯主义的复兴”中,提出了一种新马尔萨斯主义,即主宰社会史的主要力量是天气和性行为,天气决定农业成败,性行为能决定人口增加的数量。勒华拉杜里解释道,长时期的严寒造成17世纪欧洲农业收成锐减,食物供应降低。家庭根据能获得的资源数量进行人口再生产,当人口增长达到农业技术设定的限制时,就会引发断断续续的生计危机。因此,新马尔萨斯主义成为理解早期现代社会的“钥匙”。在1973年法兰西公学就职演说中,勒华拉杜里进一步深化了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他认为,饥荒与瘟疫、战争、流行病、晚婚一样,成为制约人口增长、实现生态平衡的内外机制。从1320年到1720年,让人口赖以生存下去的粮食产量持续受到这一机制的制约,因此人口和粮食产量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7世纪的法国,战争、瘟疫充当了仲裁者的角色,使人口不会超过资源的承受能力。
由此,勒华拉杜里突破了境地研究的框架,把气候当作一个外在的能动因素来研究,并形成了一种研究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范式。笔者称之为“气候的历史”,即其研究对象仅是气候的变化,不讨论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这也就是在学界引发种种误解的“没有人的气候史”。
那么,勒华拉杜里为什么提出“没有人的气候史”呢?笔者参照勒华拉杜里的著作、回忆和访谈,以总结其原因。
首先,法国主流学界受气候固定论、气候稳定论传统的影响,一些学者对研究气候变迁嗤之以鼻。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都将勒华拉杜里的研究称作“伪科学”(fausse science)。和虽然都尊重他的著作,但认为这不过是一项“业余爱好”;索邦大学说不上有什么不赞成,但是与他保持距离。因此,他觉得当务之急是证实气候在发生变化。
其次,勒华拉杜里和年鉴学派史学大师费弗尔、布罗代尔一样,都从法国人文地理学创始人白兰士那里吸取了“或然论”。他还发现E.W.埃伦海姆(E.W.Ehrenheim)、伊格纳西奥·奥拉格(Ignazio Olagüe)、爱德华·勒达努瓦(Edouard Le Danois)、埃尔斯沃思·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古斯塔夫·乌特斯特姆(Gustav Utterstrm)、E.布吕克纳(E.Brückner)等学者牵强地从气候波动角度解释人类历史,得出了一些鲁莽的结论。例如,布吕克纳以飓风路线的偏移和地中海地区土地的干涸来解释罗马帝国的衰亡,亨廷顿通过中亚干旱区域的降雨量和气压的波动来分析蒙古人的迁移。因此,勒华拉杜里认为,“气候史的目的不是解释人类历史,也不是以一种简单的方式考虑这种或那种伟大的情节,即便这种情节激发了历史爱好者的反思”。他认为,就像经济史家应该给专业经济学家提供基础史料那样,气候史家也应该给气象学家、冰川学家、地球物理学家提供史料。历史学家受过职业训练,通晓古文字和拉丁语,掌握专门的技艺,可提供某些资料。因此,他为气候史设立了这一切实可行的目标。
最后,勒华拉杜里致力于历史学的科学化。1973年,他受聘担任法兰西公学现代文明史讲席教授。在以《静止的历史》为题的就职演讲中,他讲道:“我想人们将会同意这样一种观点,使用科学的方法去对待历史学,可以让我们远远地超越对机会、事件和阴谋在人类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所作的思考,而这种思考是社会学不屑一顾的……因此,冒着被人们指责为唯科学主义的危险,我今天要在这里为这样高尚却原始的事业做一番辩护。”他想创建科学的历史气候学,“要像人们研究自然科学那样研究历史”。由此,勒华拉杜里提出要使用气象学、生物学和计量史学的方法,建立连续、同质、可计量的气象资料系列,而避开使用那些记载了大量极端气候事件的叙述性史料。勒华拉杜里认为,以往气候史学者使用的叙述性史料主要记载的是极端气候事件,是主观、异质和不连续的。他认为,“一只燕子飞来不能证明春天来了。一系列灾难性的严寒天气如果有数年的间隔,也不能先验地被认为是一个寒冷的时期”。
2004—2009年,勒华拉杜里推出三卷本的《气候的人文史与比较史》,从饥荒和瘟疫视角系统探讨了公元1000年以来西欧气候波动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由此完成了从气候的历史到气候史的转变。
这一转变是否属于1979年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所说的“从科学的历史学到叙事史的转变”呢?作者觉得,在某一些程度上,勒华拉杜里确实受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史学新思潮的影响。当时,以结构主义为支撑,使用计量方法的科学化的历史学陷入危机,叙述史和事件史有复苏的迹象,学者们不再热衷于研究长时段、静止不变的事物,而是对历史上的灾难、断裂和变动充满了兴趣。皮埃尔·诺拉早在1972年就发表的一篇论事件史的文章,于1974年以《事件的回归》为题被收录在他与勒高夫合编的三卷本《研究历史》中。菲利普·茹塔尔(Philippe Joutard)于1986年组织研讨会探讨“事件”,阐明短时段和长时段的辩证关系,指出“所有事件都是重构集体记忆的某种方式”。勒华拉杜里也投身于这一学术潮流中,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和1979年出版的《罗芒狂欢节》就是重视叙事的微观史学的典范。
但是,勒华拉杜里迟至21世纪初才开始研究气候史。他进行微观史学创作的20世纪70年代,也正是他倡导科学的“气候的历史”的年代。因此,我们应该撇开外在的史学新潮的影响,从勒华拉杜里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中,探究他从气候的历史转向气候史的动因和机缘。
据勒华拉杜里回忆,他转而探讨气候的人文史与比较史,是因为现在学者们已经打消气候史是伪科学的看法,而且肯定了他的研究。布罗代尔和拉布鲁斯主编的《法国经济与社会史》这样评论道:“多亏勒华拉杜里的研究,气候史很风光地进入法国社会经济史领域。透过长时段内冰川的增长与消退、收成的早熟与推迟,来研究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能让我们建立一系列指数。”即便是早年因研究志趣和政治立场不同,而与勒华拉杜里分道扬镳的盖伊·勒马尔尚(Guy Lemarchand),后来也认识到前者气候史研究的价值,还为其《气候的人文史与比较史》撰写了书评。
此外,勒华拉杜里多年来始终没脱离社会经济史。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成书《朗格多克的农民》,后来参与撰写了杜比和阿尔芒·瓦隆(Armand Vallon)主编的《法国乡村史》第2卷、布罗代尔和拉布鲁斯主编的《法国社会经济史》第1卷,随后又出版了《法国农民史:从黑死病到大革命》和《旧制度的法国农民:14—18世纪》。上述著作都涉及气候、歉收、谷价和人口,由此他积累了气候和人口危机的史料,也及时跟踪到学界的最新动态。另外,作者觉得勒华拉杜里的史学转变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欧洲其他几个国家的学者纷纷肯定了叙述性史料的价值,并提出了对其量化的方法。1978年,英国学者英格拉姆、昂德希尔和威格利在《自然》发表文章,指出叙述性史料有助于研究极端气候事件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并提出对其做鉴别量化的方法。瑞士学者普菲斯特同年发表文章,探讨了18世纪瑞士的气候与经济。他认为,同时代人留下的气象日记描述了天气对收成、饥饿和高死亡率的影响,学者们可以对其中提到的风、雪、雨、电的频率进行量化,如果再与19、20世纪的气象观测数据记载的平均每年雨天的数量相对比,即可判断日记的记述是否真实。英国学者帕里提出相似的方法,即“追溯法”(retrodictive strategy)。首先,使用当今天气对收成影响的相似数据,追溯历史上气候波动对农业产量的影响。其次,制作模型分析历史上的经济活动与天气变化的关联,呈现出气候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过程。1981年,荷兰学者德弗里斯认为,可以把对时间系列(time-series)的分析用于研究气候、经济或其他社会变量,通过回归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再加上比较研究,量化人类社会对气候波动反应的幅度。他把偏离平均温度超过一定幅度的气温设定为“极端温度”,以此来评估近代荷兰的冬天对经济的影响。1634—1839年,共有73个年份出现了极端温度,其中35个年份的极端温度不高于零下0.1摄氏度,38个年份的极端温度高于3.7摄氏度。1987年,比利时学者亚历山大依据叙述性史料建构了1000—1425年同质的、连续的气候波动系列。
二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社会的风险意识增强。1981年,法国政府设立研究与预防自然风险总署(Commissariat à l’étude et à la prévention des risques naturels majeurs),由著名政治人物塔齐耶夫(Haroun Tazieff)任署长,吸纳工程师参与,以整治河道、应对灾害。1982年7月13日,法国政府颁布了一则法令,规定要向自然风险受害者提供赔偿。1986年,研究与预防自然风险总署发展成环境部下设的重大风险委员会(Délégation aux risques majeurs),致力于在全国建立预防和应对自然风险的政策。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环境部和欧盟也资助了一批相关课题。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的《风险社会》从学理层面考察了工业社会面对的各种风险。同年,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的爆发使得环境风险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话题。
在这种背景下,法国地理学、水文学、气象学、历史学领域的学者纷纷转向自然灾害研究,其中一批学者探讨了极端气候事件所造成的自然灾害及其应对措施。1993年出版的《近代法国南部的气象与自然灾害》是1992年蒙彼利埃三大现代史中心召开的“近代法国地中海地区的气象学与自然灾害”研讨会的论文集,探讨了近代法国南部频繁爆发的自然灾害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应对。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法维耶主编的《历史上公共权力对自然灾害的应对》也是一本会议论文集,与会学者来自历史学、地理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建筑学所有的领域,采用以历史学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探讨了法国从中世纪至21世纪一系列应对自然灾害的公共政策的出台背景。埃马纽埃尔·加尼耶2010年出版的专著《天气紊乱:欧洲五百年冷暖》,探讨了近代欧洲对极端气候事件所造成的自然灾害的相关应对和治理。
邻国学者在气候史研究上的推陈出新为勒华拉杜里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支撑,促使他最终走进气候变迁与人类社会关系的研究领域。勒华拉杜里在回忆他的气候史研究历程时提到,1978年英格拉姆、昂德希尔和威格利在《自然》发表的文章首次定义了“历史气候学”(climatologie historique),其研究对象既包括气候的变化,也包含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与人类历史的关系。这一定义得到休伯特·兰姆(Hubert Lamb)、普菲斯特等学者的支持,也平息了某些人的质疑,这些人一直想维持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断裂,即以一种武断的方式使人类科学与自然科学分离。因此,勒华拉杜里认识到,从今往后,气候史可以堂而皇之地探讨气候变迁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法国学界自然灾害史研究的方兴未艾引发了勒华拉杜里的持久关注,也启发他从自然灾害的视角思考极端气候事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勒华拉杜里的《历史学家对气候史与“气候—危险”局势下当局态度的研究》一文,谈到了路易十四对自然灾害的治理措施。他指出,1661—1662年饥荒期间,路易十四下令去布列塔尼购买谷物,这种政策相较于黎塞留和马扎然时代是一个创新。从广义上说,勒华拉杜里的《气候的人文史与比较史》所研究的内容也可以被纳入自然灾害史的范畴,该书使用了大量叙事性史料,梳理了13世纪至21世纪初西欧发生的一系列极端气候事件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近年来,勒华拉杜里更为强调自然灾害史与气候史的关联,在2011年出版的《公元一千年至今的气候波动》中指出,气候史不仅要研究跨越一个或数个世纪的冰舌的移动和延续几十年的气温的变化,还要关注零星出现的、短则几个月长则一两年的气候事件。当前学界把后者纳入“灾害”(catastrophes)的范畴进行探讨。
勒华拉杜里从气候的历史转向气候史并不是对科学的历史学的否定,而是为了把科学的历史学与叙事的历史学结合起来,探索一种总体史。
总体史是年鉴学派的追求。费弗尔说,新的历史学是“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研究人类的全部活动。它利用人类的一切创造物和所有可利用的史料,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方法,避免分割为许多专门的部分(思想史、经济史等)。布洛赫认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的全体人类”,他的总体史设想就是运用语言学、比较文学、民俗学、地理学、农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研究人类生活的总体面貌。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将总体史研究推向顶峰。虽然年鉴学派第三代史家围绕总体史产生了分歧,但勒高夫、古贝尔、瓦絮代勒、贝桑松、勒华拉杜里等学者还是坚持总体史的研究方向。
勒华拉杜里对总体史的探索贯穿其整个学术生涯。《朗格多克的农民》渗透了他的总体史理念,试图综合社会经济史和心态史。他在导论中写道,他从研究土地目录开始,最终走向思考活生生的人,探讨朗格多克的农民群体。物质史和计量史虽然很严格,但只提供了一个很粗糙的网状结构,因此,他想通过关于农民骚乱的编年史,通过乡村宗教的血腥历史,探讨一个人群的历史,进行总体史的探险。该书第二部分的总标题是“意识与社会斗争”,探讨了16世纪农村贫困化过程中各阶层的反应及其心态,研究了巫师狂欢日和1580年罗芒狂欢节,前一主题在《蒙塔尤》又出现,后一主题又被拓展成《罗芒狂欢节》。《蒙塔尤》是微观史学的代表作。勒高夫说,所谓微观史学,即把“‘一块历史’当成一个标本,将其视为洞察整体的历史的一个微型景观(miniature)”。《蒙塔尤》同样是勒华拉杜里在总体史视野下进行的写作。从时段上来说,该书由长时段历史中的蒙塔尤和1294—1324年的异端审判事件两大部分所组成,与布罗代尔的名著《地中海》暗中呼应;从内容上说,该书既阐述了蒙塔尤的生态,也考察了蒙塔尤人的行为举止、交往模式和社会结构。
第一,从研究内容上来说,该书结合了自然史与人类史。在整体结构方面,一方面凭借葡萄采摘日期数据和描述性史料,重构了西欧13世纪以来一年一度的精确的气候波动系列,并在此基础上结合阿尔卑斯山冰川的消融或增长,总结出气候的中时段和长时段波动。另一方面系统考察了西欧13世纪至21世纪初所发生的一系列极端气候事件及其对小麦收成、粮食价格、人口增减等方面的影响,还探讨了法国历史上一系列重要事件爆发的气候背景。在资料来源方面,该书系统地吸收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成果。关于蒙德极小期的论述,勒华拉杜里借鉴了德国天文学家F.W.G.施珀雷尔(F.W.G.Spörer)、英国天文学家E.W.蒙德(E.W.Mauder)和德国气象学家于尔格·卢特尔巴赫尔(Jürg Luterbacher)等学者的成果。针对1314—1315年的大饥荒,勒华拉杜里参考了美国非裔历史学家威廉·切斯特·乔丹(William Chester Jordan)关于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时期的饥荒和生计危机的论述,还借鉴了法国历史学家让-伊夫·格勒尼耶(Jean-Yves Grenier)、弗朗索瓦·勒布伦(François Lebrun)、吉尔斯·贝尔纳(Gilles Bernard)、伊夫-马里·贝尔塞(Yves-Marie Bercé)、马塞尔·拉希韦(Marcel Lachiver)等人的研究成果。
第二,从研究地域上来说,该书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范围。在年鉴学派的视野里,总体史的一个维度是全球史。早在1973年,勒华拉杜里在《瑞士历史杂志》上发表文章,探讨了中世纪中亚地区出现的巴斯德式杆菌是如何通过藏身在商贩的毡毯中或老鼠身上的跳蚤,而传播到西欧并引发瘟疫的,从而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出现了“疾病带来的全球一体化”。《气候的人文史与比较史》进一步呈现出勒华拉杜里的全球史视野,探讨了同样的气候事件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产生的不同影响。他分析道,1586—1587年的生计危机在某一些程度上影响了英格兰,而法国南部夏季炎热的天气缓解了多雨所造成的危害,使法国的阿基坦(Aquitaine)地区幸免于难。他还探讨了1921年热浪对美国和欧洲造成的不同影响及其原因。在欧洲,炎热、干燥对牲畜的影响很大,但小麦与酒的生产均量足质优。而在美国,干旱发生在离大洋很远的大平原上,所以小麦的生长受到了很大影响。
第三,从研究方法上来说,该书超越了单一因果模式,从多个层次来解释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首先,勒华拉杜里把气候因素的影响放在经济、文化、政治、宗教和科学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情势中进行深入分析。例如,他探讨16世纪后半期气候危机的影响时,指出安茹、多芬内、佩里戈尔(Périgord)、拉罗谢尔和普瓦图受宗教战争的影响,阻碍其谷物从乡村被运往城市,由此加重了生计危机。又如,在分析气候与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关系时,勒华拉杜里首先探讨了1788年的极端气候事件所造成的粮食减产、物价上涨和心理创伤。随后,借助勒马尔尚和雅克·戈德肖(Jacques Godechot)的研究,分析了1789年7月11日至7月14日之间,国王罢免雅克·内克尔这一政治事件与谷物昂贵这一经济问题如何联合起来激发了巴黎民众的反抗情绪,最后导致巴士底狱被攻占。其次,勒华拉杜里注重分析各地不同的天气特征情况或应对措施所造成的不同影响。例如,1661年的多雨天气令法国北部和西部(布列塔尼除外)受灾严重,法国南部则因干燥、温热而没有遭灾,贝济耶市场的小麦价格甚至会降低。法国政府的救援措施也制约了灾害的影响力。在1661—1662年的灾荒中,官方将从波罗的海或布列塔尼运来的谷物先输送给城市,他们都以为那里的社会动荡比乡村更可怕,结果对乡村造成更严重的影响,农民只能靠救济为生。
第四,从写作体例上来说,该书采用了全景画似的写作手法。年鉴学派倡导的总体史是整体的历史,即将一切可搜寻到的材料合理地汇总起来,呈现出能够解释历史制度的性质和运作的整体结构。为了从整体上把握气候变迁的趋势,勒华拉杜里通过冰川的增长与消退,将西欧9世纪至21世纪初的气候变迁划分为中世纪暖期、小冰河期与气候回暖三个长时段。该书不仅依次探讨了从14世纪以来西欧每年的气候波动,总结出每个世纪内十多年、数十年的气候波动趋势,还探讨了14世纪以来每一起重要的极端气候事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以及法国历史上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或事件的气候背景。如果说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从地理空间到结构局势再到政治事件,由远及近地展现了菲利普二世时代地中海世界的全景画,勒华拉杜里的《气候的人文史与比较史》则呈现出一幅14世纪以来西欧气候变迁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全景画,师徒二人皆在年鉴学派的总体史书写中为读者提供了一部关于地中海或气候史的“百科全书”。
总之,勒华拉杜里通过对气候史的研究,实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计量与叙事、结构与事件的结合,推进了年鉴学派的总体史探索。由此能够解释,20世纪60—70年代,勒华拉杜里倡导的“没有人的气候史”与他21世纪初致力于构建的气候史并不矛盾。如果说三卷本《气候的人文史与比较史》标志着勒华拉杜里总体史探索的完成,“没有人的气候史”则是他进行总体史探索的一个阶段,其研究成果也被后期著作所吸收。因此,总体史是勒华拉杜里一以贯之的追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始终强调自己是布罗代尔学术遗产的继承人。
当然,勒华拉杜里的气候史研究有其局限性。虽然《气候的人文史与比较史》的叙述范围常常超越法国,涵盖欧洲,有时还将美国、非洲、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纳入其中,但没考虑亚洲的情况。而竺可桢的宏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则勾勒出3世纪以来欧洲和中国温度升降变化的关联,杰弗里·帕克的名著《全球危机:17世纪的战争、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与灾难》从全球气候恶化的背景分析了17世纪危机对各国的影响。这些著述都提示我们,有可能从更广阔的地域范围进行全球气候史的研究。